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而互害现象则相反,就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就涉及了儒家的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了。

儒家之义实质上有两条正义原则: 1、正当性原则 孟子指出:居仁由义……仁,人之安宅也。[29]互害问题也是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回到前现代的道德与制度,而是建构现代性的道德与制度。[14]《荀子·子道》,王先谦《荀子集解》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22]《礼记·中庸》,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例如儒家经典《周礼》之礼,就是讲的一整套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
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利,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不负责任,也就没有市场道德、现代道德可言。儒家对制度规范之礼的认识有两个层面: 1、礼的普遍正当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所谓五行四时等等,虽各有其性,然都来源于原型的太极,归本于更本源的无极,也就是周敦颐所强调的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无论仁或义都有着天的形上本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正是宋儒从形上学与宇宙论衍生出来的价值信仰,决不怀疑人性中即蕴藏着形上超越的内涵,经由人的德性生命的实践活动必可臻至圣境,自孔孟之后由周敦颐率先重新奠定其立论的大根大本,明显蕴涵着极为深刻的天人合一理论言说向度(88)。伊川所谓圣人本天,释氏本心(12),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实已道出与天道观有关的形上学与有机宇宙论在北宋儒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遂不能不以此作为区分儒佛两家思想立场的一大衡量标志,突出地反映了儒家学者要将天理或天道落实于人间社会的价值维度和实践路径(13)。宋说见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卷二十四中丞宋望之先生仪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7页。
而纯者不杂之谓,心谓人君之心,言君天下而欲兆民一于善,只在纯一人之心而止矣(96)。也就是说,宇宙生成秩序的具体节律化运作,必须凭借理气交相融合必然展现的力量动因,透过阴阳、五行、四时等一系列过程,才能产生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的现象,并按照其不同的性质、类别、功用等等,形成了林林总总复杂万千的客观事物。

因而正君心在以周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看来便是正天下,是从权力发生的行为源头来建构秩序的一种有效路径或方法。(70)以上均见《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所附朱熹注,《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第76、76页。(56)《通书·师第七》,《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第69页。因而由中的本体发出的道德实践行为,必然是正而不偏,能够实现德性生命固有的仁义价值,达致人道与天道一体不二的终极性价值目标的。
而秩序治理责任之所以要由君主来主动承担,则是因为其为权源结构的核心要害,不能不说是天下之大本在于君,君正则意味着天下参与秩序建构的人无一不正。但如果逆溯其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源,则都是无极而太极的展开,是本体既超越又创生,最终显现为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的必然性结果。而二气五行,天之所以赋受万物而生之者也,凡天之所授,即可称之为命。(74)太极既是总摄一切的整体性大全,又是贯道天下的一理,因而任何分殊都不可能是脱离大全的孤立的存在,有违一理的毫无根据的荒谬他物。
⑩周敦颐对二程、朱子影响之大,殆不必多言,即对后来晚出之阳明,沾溉亦颇为深厚。周子直承先秦儒家精神传统,以为天的生物之道即为仁,成物之道便是义。

(12)(68)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附师说后,《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4页。形上统一的天道本体总是以创化或成就万千差异性的事物的方式来开显式地隐蔽自身存在,差异性的事物则总是以共同的生生不息之理来隐蔽式地开显形上统一的天道本体的存在。
而自宋儒揭出天人合一之旨以后,历代学者讨论颇多,贡献发明亦不少,然追本溯源,仍可说滥觞于先秦,大盛于宋明,遂形成了极为系统的天道观与心性论,反映中国哲学思想始终内涵着丰富的宗教意蕴,决非其他任何肤浅的俗世学说能够比况。这一模式尽管缺乏心性论的哲理奠基,较少人的道德自觉心的点醒或提撕,难免不有一种以灾异附会人事的神秘主义色彩,但由于更多地突出了以阴阳五行等一系列范畴建构起来的有机宇宙论思想,仍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恢宏阔大的精神气象,而与汉代大一统帝国文化的声威气势相契应。天地既然是人的仿效对象,因而天道的行仁义与圣人的修仁义,虽一表现为万物顺,一指向万民化,行为现象的展开似乎略有所不同,但形上本体的根源却无二致,完全可以立人极的方式,做到尽人事以合天道。刘说见《刘宗周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周子力图将与天道本体相通合一的道统引入代表权力世界的政统,显然也为后来的理学学者重新开出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结合的思想发展新路径(112)。因而必须以人合天,才能德配天地。
既然人与天地万物都无不统归于整体而大全的终极性太极,作为有主体自觉精神的人,当然就应该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103)而较张载更早立说的周子,也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即在养心,养心的根本则为立诚,立诚即是自觉其性并实现其性的过程,当然也是契入自我本体之真与万物存在之真的一种方法。
太极固然是一切创化力量的总体源头,但也非高高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人格化主宰,而是内涵或寄寓于一切事物,同时又统摄或超越于一切事物。(42)曹端:《太极图说述解·死生诗》,《曹端集》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第22页。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98)。人只有最大化地扩大自己仁民爱物之心,才能做到德行浩浩然堪配天地。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周敦颐的一实万分,万一各正,明显便是理一分殊处(71),前引朱子月映万川之说,便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72)。以无极为原型本源,或者说从无极而太极出发,分析宇宙自身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发展过程,周敦颐以生生为根本原则,建立了他的一整套天人相贯互通的解释模式。(20)(24)(43)(45)(76)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太极图说》,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133、2130、2144、2125、2130页。
显象的序既有形又有理,当然就能表现为万事万物的自然秩序规则,同时也透过人性固有的理性秩序原则,显象为可观察和经验的伦理生活秩序。(91) 十分明显,周敦颐不仅要将本体论与价值论打通,从而强化人的道德实践,更重要的是还要将道德实践扩大至政治场域,以实现儒家一贯持守的德化理想。
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便已明白指出: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己,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立场讲,则可说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纯其心,斯成大顺大化,法天为治也(97)。
……诚精故明,神应故妙。朱熹以为仁、义、礼、智乃五行之德,动静为阴阳之用,言貌、视听则应属五行之事(94),显然也是立足于人道与天道不可二分而发论(95)。
张新民:《生命成长与境界自由:〈论语〉释读之一》,载《孔子研究》1998年4期。从他的理路脉络看,诚本身即有纯粹至善即存在即超越的品性: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按周敦颐《通书·圣第四》亦提到寂然不动,诚也。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已不难知道,太极与现象界林林总总的事物的关系,实乃是万为一,一实为万即一多不二的关系。
因此,尽管周敦颐主要关注宇宙论,而较少涉及心性论,或许可能淡化了人的主体性,但从他的哲学形上学视域出发,仍可见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大生命系统,不仅在宇宙生成论上本来一体同源,甚至相互之间亦有必须共同遵行的本体论原则。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周敦颐极力强调诚在本体论与工夫论两方面的重要。
(28)《周易·系辞上》,《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31)黄犁洲:《太极图讲义》,引自《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9页。
稍后《郭店楚简》明确提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③,则更进一步深化了人的存在与终极超越的天道的内在关联。(35)(78)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天地,《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1226、12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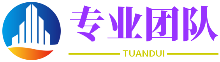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